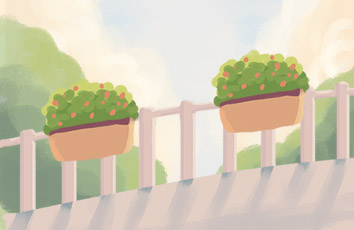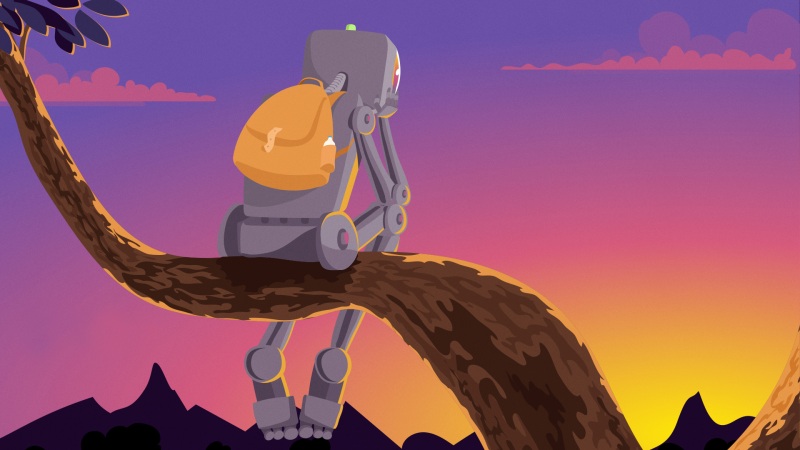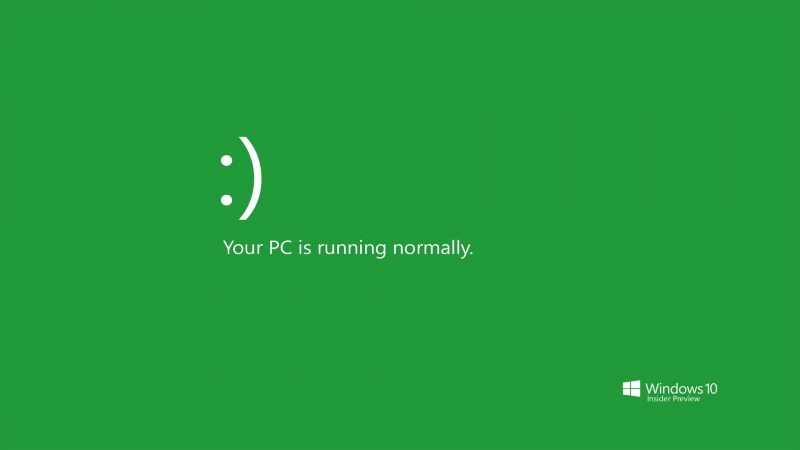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7937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6 分钟。
前言:
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凭籍着《午夜北平》(Mid nightin Peking)一书中生动的叙事与严谨的考据,渐为汉语世界的读者所知。本书《恶魔之城》(City of Devils),延续了法兰奇一贯的写作风格。作者通过对工部局档案、英美领事馆资料、美国在华法院记录,以及当时的报刊等原始文献的整理,试图构建文本中记叙的日据前夕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图景。《恶魔之城》一书除序幕、尾声外,共分为三个部分。法兰奇通过对杰克·拉莱(Jack Riley)与乔·法伦(Joe Farren)两人发家史的细致观察,为读者了解上海“孤岛”的政治运作、司法系统、自治组织,以及夜总会、赌场、酒馆的经营现状、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提供了独特的阅读窗口,实属精彩的普及读物。但是不同于他人对法兰奇出色叙事技艺的着迷,笔者更欣赏法兰奇对被欧洲中心主义、殖民话语所笼罩下的上海租界研究的低姿态的反抗。
法兰奇虽然不是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史学者,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但是他紧跟着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1]等杰出海外中国学学者的话语范式,自觉地遵守着史学研究的规范,这些“习惯”为他的非虚构类近代中国犯罪文学的写作提供了精致的学术外衣。更难能可贵的是,法兰奇对近代外侨当局档案材料的吸收上,刻意避免着东方主义与殖民话语的再生产。对笔者而言,本书最吸引之处在于“孤岛”所展现出自治组织的蓬勃生机以及“孤岛”形象的错综复杂[2]。本文谨就笔者对本书所带来的问题意识与不足之处,略加申述,以祈就正大方。
本文作者亭,原标题为《塑造孤岛:日据前夕上海租界的暴力、秩序、自由结社与形象建构》。
恶魔之城: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地下世界
01
殖民话语下上海租界的形象建构
近代上海租界形象的生产,本身就是国际体系演变的结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混杂着盘根错节的多方势力[3]。上海租界的形象,离不开多方力量的相互塑造。在日本强硬派看来,上海是中国内陆势力抵抗日军深入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前者作为国际势力的远东枢纽,包含着不确定性。正如古厩忠夫将上海与重庆、延安并列为日本侵华战争发动以来,中国本土抗战的三级构造。“上海租界的面积虽然只有30平方公里左右,但在日中全面战争的一半以上的时期内,持续了“孤岛的繁荣”,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钉,并且成为迫使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的一大要因。在考虑重庆政权的抗战力时不能将上海排除在外。在与新四军的关系上也同样如此。当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上海的这一事实也不能忽略。同时,由于上海租界是反映围绕日中战争的国际关系的一面镜子,上海的研究告诉我们,日中战争是一场国际性争”[4]。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看来,上海远东局肩负着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工作、推广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使命。因此上海更像是莫斯科将意识形态与政治模式向中国、朝鲜、日本、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的桥头堡。然而在英美外侨看来,上海是一座充满机遇、财富、权力、艳遇、混乱的磁铁,源源不断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金融精英、冒险家、流亡者、难民。法兰奇在本书中这样描写道“恶魔之城”的独特魅力,“这座弱肉强食的城市是一块磁石,吸引了冒险家和游手好闲者”,“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大有前途的冒险家,怀着共同的简单信念——‘钱’以及‘挣钱’——走到一起”。对于英美等国政府当局,上海租界的繁荣被视为是对自《南京条约》以后长期建设性努力和莫大的资本投入的结果[5]。多元的视角构建了不同的叙事与想象,上海公共租界的命运也紧跟着殖民话语的塑造历经坎坷。
当上海租界被英美的殖民精英视为中华民国与国际势力之间政治控制、经济互动、文化管理的缝隙时,上海为不同文化的共处、交流、融合提供了土壤。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观察到,上海所具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的边缘性特点,在总体上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和宽容性,由此使上海在面对西方文化涌来时显得比较从容和大度[6],而在这种互动中,公共租界处于东西文明交流的前沿阵地,最为活跃。英美等国将自己的政治传统移植到了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公共租界实行自治,选举工部局自我管理,组织“万国商团(ShanghaiVolunteers)”,维护自治。在传统国家力量难以渗透的缝隙中,多种力量势均力敌的相互掣肘,反而使表面混乱的上海公共租界涌现出了稳定的秩序,直到日本人的介入武断地打断了这种政治实践,使得上海租界的形象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图源:https://unsplash.com/photos
02
怀乡病、参与权与权力化叙事
“八一三”事变[7]前,上海的日本各方势力极其分化,大致可分为“强硬派”与“国际派”,其中公共租界中的日侨居留民大多属于前者。上海公共租界的形象在日侨居留民心中,产生出与英美外侨类似的“乡土”情结。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秘书长,高纲博文教授在他的论文《<我的故乡·上海>的诞生:有关上海日本人归国者们怀乡情结的考察》中,仔细地考察了曾经在上海居住或出生在上海的一批日本归国者对上海怀乡感情的生成和发展背景。[8]这些日侨居留民通过日常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型塑了公共租界的政策生产。比如在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后,不仅仅是中国方面,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也对租界行政进行批判,要求改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9]。1935年10月,上海日本居留民向租界当局(工部局)提出对公共租界行政改革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市参事会员选举制度的时代性错误及非民众性。
2.作为行政中枢的工部局职员中英国人占绝对多数,其机能颇具寡头政治的色彩。
3.行政费用数额巨大,尤其是俸碌支出有过当之处。而且对义勇队、警察、教育、音乐及其它各部的不必要支出较多。
4.租界预算,尤其是教育费,未能实现各国居留民间的平等分配。[10]
高纲博文教授指出,提出上述要求的日本居留民,长期居住上海公共租界,在“疏远感、孤立感、被害者意识”的基础上,组织产生了上海居留民自治团体[11]。这些异乡的“乡土感”,让日本居留民产生了排他的异乡民族主义,当这种民族主义与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运动相遇,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1940年4月10日和11日,日本人翘首以盼的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在工部局大楼及虹口市场三楼进行了投票。[12]
日本在临近选举的时候制定了以下两大方针:
(一)必须根据新形势,对传统的英国人垄断的租界行政加以修正。
(二)必须在董事会反映出日方的正当发言权,并对工部局机构及其财政问题作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日方推出五名候选人参与竞选,比以往多出了两名。
对此,英方自3月中旬开始秘密地与美方商议对策,以期扩大选票数,从而占据选举主动权。此次选举,日方共推荐了五名候选人(冈本一策、黑田庆太郎、冈本乙一、高雄太郎、田诚)参加选举,结果仅两人当选,不可不谓失败。[13]本次选举不仅备受当地的关注,日本国内的各大报纸均以之为重大新闻,并注目于选举的结果,足见日本对上海的重视程度。此次选举是在汪伪新国民政府成立后(1940年3月30日)不久进行的,如果选举成功,将大大有利于日本与汪伪之间的合作。因此,对于日本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选举的结果使日本深感失望,因为日本谋求在公共租界行政方面扩大发言权的企图遭到了不小的挫折。[14]
当他们试图通过公共租界内部的政治规则来提升日侨地位、扩张日侨权利的诉求[15]失败后,便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措施——与“华北事变”之后急速发展的日本国家势力合流。遭到选举失败的日本居留民对租界当局的反感情绪日益高涨, 他们威胁租界当局 :“居留民知道日军反对租界当局 ,就迎合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越轨行动, 甚至发展为武力行动”[16], 不停地给租界当局找麻烦。[17]
图源:https://unsplash.com/photos
03
法兰奇笔下上海租界的暴力、混乱与地下世界
回到《恶魔之城》本身,法兰奇笔下的上海租界的形象,便是欧美外侨所建构出的“恶魔之城”。作者在本书中的致谢中提到,书中记录的上海轶事来源于Robert Bickers、Douglas Clark、Andrew Field、Fred Greguras等居住上海外侨的回忆。以及对工部局警务工作、乔·法伦、百乐门演出的了解,来源于当事人的后裔、亲人。这种视角的复制也塑造了本书作者欧美侨民的叙事视角。“恶魔之城”在法兰奇看来,同样是欧美世界边缘的机遇、财富之城。乔·法伦与杰克·拉莱二人的发家史,是法兰奇透视上海租界地下世界的棱镜。杰克·拉莱作为一名孔武有力的前美国海军士兵,在俄克拉荷马州惹上官司后,越狱亡命菲律宾马尼拉。并将在美国西海岸与马尼拉学习到的赌博作弊技术与老虎机经营带往了上海,从而为后来成为“老虎机之王”构建了技术背景。
杰克·拉莱与乔·法伦的成功离不开公共租界所预留的自我表达的巨大空间。上海公共租界的政治结构,是传统国家权力消退,自发组织借助国际势力的干预渗透,进而浓郁成长的结果。由于上海远离欧美本土,类似英国与美国的政策法令很难有效约束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当局与各方势力,类似三十年代美国本土实行的沃尔斯特法案[18],自然而然受到上海公共租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抗。而作为上海领土主权拥有者的国民政府,在国际势力的强势介入下,其政策更难以影响公共租界的日常运作。当蒋介石的禁烟令在上海(非租界)执行,纽约黑帮老大小路易斯·布切尔特(Little Louis Buchalter)便联合上海青帮杜月笙,重新制造了毒品供给线。正如保罗·法兰奇所指出的“只要这座城市还矗立在黄浦江两岸,毒品就会沿着它的血管流动”。毒品的猖獗归因于政治空间的破碎性,为黄赌毒产业的野蛮生长创造了温床。在这种弱权力的社会空间中,租界生活的人们很难感受到政府自上而下的管制与当局者的权力意志,反而是这种地下世界的黑帮、毒贩更能左右租界的经济走势、文化产业、政策决策。
图源:https://unsplash.com/photos
04
日军对“恶魔之城”形象的改造
上述“弱权力”的政治结构在“上海事变”发生后,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日本“强硬派”试图利用国家主义的政治理念,重新塑造上海租界的政治结构,为日军最终占领、管制上海全境创造政治合法性。蒋介石与他幕僚对租界的设想[19],随着战争的失控而崩溃。上海租界事实上已经成为日本“妨碍进行圣战的不可轻视的障碍物”[20],并且日本东京政府官方学者植田捷雄责难租界中立态度的合法性“本来,租界在国际法意义上并不具有能够主张中立的法人资格,有关租界的中立,也未曾听说过有相关的国际约定的存在。这只不过是外国的一面性主张而已,其根据是非常薄弱的。”[21]随着日本与英美等国矛盾的加剧,“租界中立”的态势得以打破。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军部就进驻细节展开讨论,其计划要点如下:
1.原封不动地保持租界的繁荣(为了尽量早日解决Cina事变,保存租界作为中立地带以便重庆政府与日本方面的接触)。
2.不侵害法租界的权限(置以中立的地位,但是,不允许成为重庆方面特务机关的根据地)。
3.上海市内成为汪精卫政府军的安居地 。
4.不拘禁敌国人(但是出入时必须佩戴日本方面许可的臂章)。
5.没收敌产(但是银行等经济、金融机构,为避免没有必要的混乱保持原样)。
6.软禁公共租界的英美外交官(但给予相当待遇)。
7.在处理租界问题的同时,约二个星期内禁止一般日本人出入。[22]
对于欧美外侨,日军的占据与改造是灾难性的,正如国内学者徐青所指出的,“在汪伪政权的协助之下,对在沪欧美人以及上海当地人实施了严格的户籍管理。据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从1941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户籍管理是日本接管租界“改造”上海的重头戏,不仅对敌性欧美人、上海人,甚至对处于城市外围的乡村也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登记…还包括辖境市民职业、籍贯、宗教种类人口以及辖境外侨国籍的调查统计…对于那些居住在上海的欧美人来说,日军进驻而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也显示出,从1942年夏天开始,日军对欧美人士的户籍管理比上海一般市民更为严厉。”[23]
值得注意的是,当日军占领租界后,不满于欧美外侨塑造的上海“恶魔之城”的形象,日本文人与媒体着力扫除上海“恶魔之城”的形象。《文艺春秋》社特派员兼从军记者西川光在文中写道:“洋鬼的时代结束了。当然,他们所播撒的恶魔的种子,不会简单地就这样被清扫干净,但是我们会不厌其烦,直到扫尽恶魔的种子为止。”[24]
(本文作者:亭,已获授权)
向上滑动阅览
批注
[1] 参见[英]保罗·法兰奇:《恶魔之城: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地下世界》,兰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419页。“我还必须感谢伟大的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1937-2006年)对上海“歹土”的研究。他的著作《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1995)]和《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1996)]使我第一次对上海历史的这个侧面产生了兴趣。”
[2]事实上,无论重庆的国民政府、国人,还是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多国的政府与民间精英、流亡者,都参与了“孤岛”形象的建构,最后脱颖而出的“孤岛”形象叙述必然伴随着去殖民化的价值裁决,这也使得原本错综复杂的“孤岛”形象,变得单薄、遥远、混乱,并成为苦难记忆的重要一环。
[3]其中本土包括革命后的清遗民、被国民政府吸收的地方势力、共产国际远东局、三十年代后期组建的汪伪政府、不被政府认可的大量非法组织。外部渗入势力包括白俄、苏俄、英美法等国政府、外侨团体、日本居留民与强硬派等多方势力。
[4]参见[日]古厩忠夫:《日中争と上海民族資本家》(叶山祯作等编《伝統的経済社会の歴史的展開》下,时潮社,1983年3月,第77-78页)。关于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租界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参照古厩忠夫:《日中争上海私》(《近きに在りて》第5号,1984年5月)及《日中争末期の上海社会と地域エリ一ト》(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重層するネットワ一ク》,汲古书院2000年3月版)。
[5] 参见[日]植田捷雄:《上海租界問題》,《華中現勢》,上海毎日新闻社,昭和15年版,1939年11月,第594页。
[6]参见《“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2002-05-20.
[7]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虽经三个月的顽强抵抗,终因实力不济,战败而退。11月12日,上海的华界以及公共租界位于苏州河以北的地区(俗称“日租界”),沦陷于日军之手。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日军没有占领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租界的主权一如往昔。于是,在日军的包围下,租界变成了孤岛。
[8] 参见《“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2002-05-20.
[9] [日]高纲博文:《战时上海的“租界问题”》,《史林》2007年01期。
[10] [日]植田捷雄:《増補Cina租界論》,巌松堂书店,1939年8月版,第342-343页。//转引自[日]高纲博文:《战时上海的“租界问题”》,《史林》2007年01期。
[11] 即上海日本人各路联合会。
[12]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40年行政报告及1941年度预算》(日文版),第3页。
[13] 4月12日,工部局公布了当选者及候选人的得票数。当选者为:阿乐满(N. F. A11man,美)、卡奈(J. W. Carney,美)、恺自威(W. J. Keswick,英)、赫兰(G. A. Haley,英)、鲍惠尔(T.S.Powell,英)、麦道南(R. G. Macdonald,英)、米基尔(G. E. Mitchell,英)、高雄太郎(日)、田诚(日)。参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40年行政报告及1941年度预算》(日文版),第4页。//转引自甘慧杰:《论孤岛时期日本对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的争夺》,《档案与史学》,2001-12-30。
[14] 甘慧杰:《论孤岛时期日本对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的争夺》,《档案与史学》,2001-12-30。
[15] 植田捷雄在《外交时报》上发表的《上海公共租界行政的批判》一文中提到:“最近,围绕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出现了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公共租界中长期以来英国占绝对势力的专断施政,我国的居留民终于团结一致崛起反抗了。”参见植田捷雄:《上海租界問題》,《増補Cina租界論》,第 340页。//转引自[日]高纲博文:《战时上海的“租界问题”》《史林》2007年01期。
[16] [日]堀内干城:《中国の嵐の中で》, 乾元社 1950年版, 第 171页。
[17] [日]高纲博文:《战时上海的“租界问题”》,《史林》2007年01期。
[18] 即禁酒法案。
[19] 参见[英]保罗·法兰奇:《恶魔之城: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地下世界》,兰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95页。“蒋委员长和他的南京政府让上海人继续抱有以下希望:也许西方列强的领事、商人和他们的军队战舰能够牵制来自东京的更可怕的威胁”
[20] 参见[日]植田捷雄:《上海租界問題》,《華中現勢》,上海毎日新闻社,昭和15年版,1939年11月,第594页。
[21] 参见[日]植田捷雄:《上海租界問題》,《華中現勢》,上海毎日新闻社,昭和15年版,1939年11月,第595页。
[22] [日]高纲博文:《战时上海的“租界问题”》,《史林》2007年01期。
[23] 徐青:《日本占领时期对上海租界的“改造”》,《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24] 西川光:《十二月八日的上海》//山下武、高崎隆治监修:《上海丛书(第12卷)》,大空社,2002年。
书籍推介
恶魔之城: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地下世界
〔英〕保罗·法兰奇 著
兰莹 译
2020年7月 / 72元
ISBN:978-7-5201-6567-9
在酣歌醉舞的十里洋场,维也纳人乔·法伦成为“歌舞表演之王”,其名字在臭名昭著的“歹土”法伦夜总会的霓虹灯牌上不断闪耀。与此同时,美国逃犯杰克·拉莱以“老虎机之王”的身份,在上海闯出一片天地。“衣冠楚楚的乔”与“幸运的杰克”犹如两颗陨石在空中轰然相撞,随后又在狂乱的挣扎中携手合作,抱团熬过这座城市彻底沦陷前的最后一段日子。他们的“友谊”充满算计与背叛,折射出上海外侨社会当时的种种怪象。保罗·法兰奇还原了上海“歹土”的旧日生活,还原了那里的种种罪恶,生动再现了一段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历史。
作者介绍
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
生于伦敦,求学于伦敦和格拉斯哥,曾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出版过多部传播甚广的分析、评论中国的专著。其代表作《午夜北平》是“爱伦·坡奖”最佳罪案实录奖项(Edgar Award for Best Fact Crime)和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的非虚构类金匕首奖(CWA Gold Dagger for Non-Fiction) 得主。
译者介绍
兰莹
先后就读于外交学院英语系、中国人民大学美术学院。现为公务员,从事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工作。业余从事文学、历史、美术领域的翻译,译有《午夜北平》等四本书。
原标题:《塑造孤岛:殖民话语下的上海租界丨书评》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塑造孤岛:殖民话语下的上海租界丨书评》,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