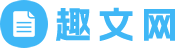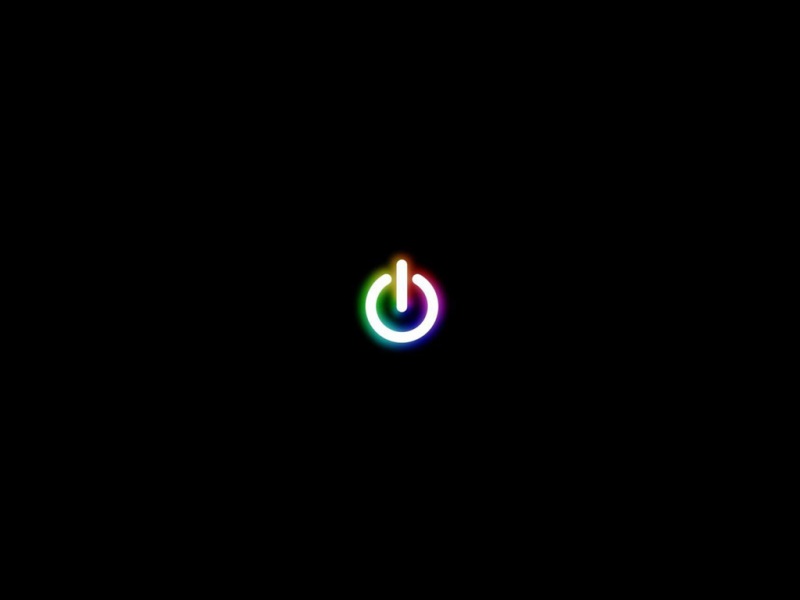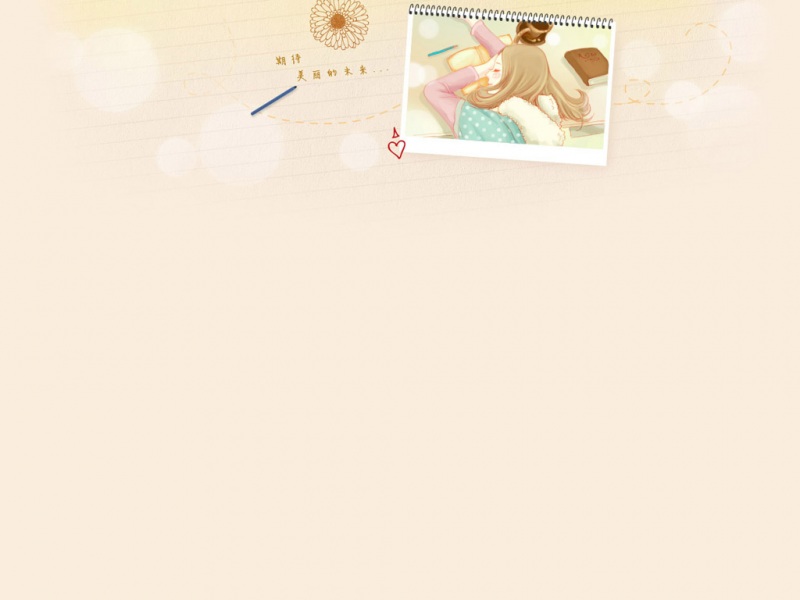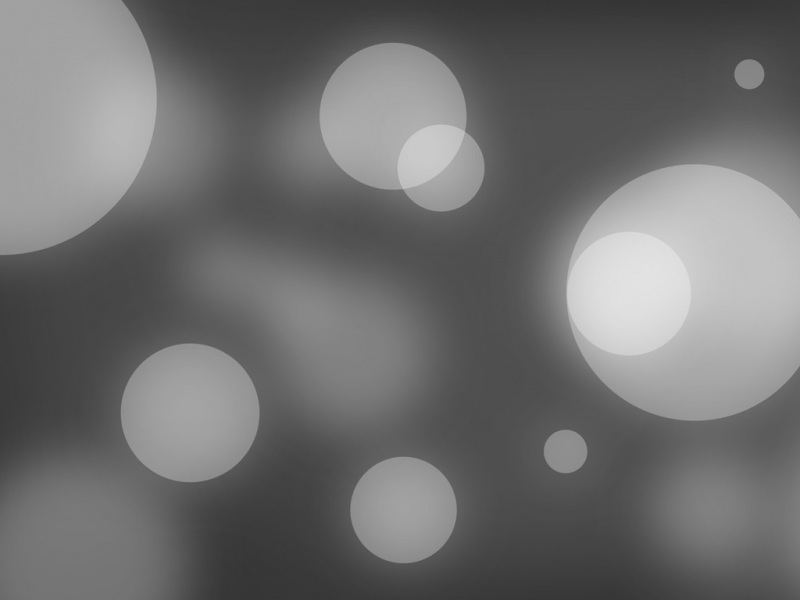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12277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5 分钟。
基督教新教首位华人牧师梁发首先是一个宗教人物,这也是历来对他的共识性评价。梁发是中国近世较早从事新教布道读物写作的“非精英人士”,印刷技术是他职业生源的起点。他在教会系统内外产生影响,则得益于他的翻译与写作能力。梁发的文体选择,是对马礼逊、米怜中文文体观的呼应与发展,也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近代文学的边界,宜从宗教、翻译、文学等多个层面认识和理解。
梁发通常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文学人物,但他在教会系统内外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布道演说和写作。[1]从本质上讲,演说和写作是一种文学的方式。梁发略懂英文,却程度有限,并不能娴熟使用。这似乎意味着,他在翻译方面不可能有所作为。然而实际上,他仍然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进行“翻译”——本文称之“间接性翻译”。一个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印刷工人,在有幸进入跨文化、跨国界的“异度空间”以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文化自我”?梁发的道路,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演进轨迹有何交织,意义如何?
△ 钱纳利绘《广州的商馆》(马儒翰石印单张)
伟烈亚力曾经尽可能详实地罗列过梁发的中文著译,但仍然不出差传史、教会史的范畴。[2]近年来,近代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与白话文学的关系问题颇受关注,但学者们的研究重心仍是马礼逊、米怜等人而很少及于梁发。[3]费南山在探讨19世纪中国的“新学”问题时,认为过去普遍聚焦于“精英成员”,而忽略了早期从事知识传播的非职业者。费南山以李善兰为例,强调这些早期口岸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混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于是不得不“穿越不同职业、社会和民族群体的界限”,费南山称他们为“19世纪中国新学领域的社会活动家”。[4]潘光哲从“知识仓库”“地理想像”“读书秩序”等层面讨论“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5]注意到传教士出版的福音书刊也是中国士人追求“世界知识”的窗口。白话文学、翻译文学、“新学活动家”、“知识仓库”等思路或提法,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传教士和口岸文人的新视野。不过他们都没有将梁发作为讨论的重点。
△ 广州岭南大学校园内的梁发墓(今属中山大学)
梁发约从1811年起从事马礼逊中译圣经的印刷,稍后随米怜前往马六甲。[6]梁发比王韬、李善兰等人更早地进入了一个跨越民族、国家、语言界限的“混杂的社会环境”。梁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科举功名,因此他后来的作为也就更值得重视。与后来的王韬、李善兰等人不同,梁发的“环境”不只“混杂”,而且危险。他两次被地方政府逮捕,挨过官府的大板,被痛打到出血[7]——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在他身上留下过真实的“血痕”。
1930年,麦沾恩在为《梁发传》所写的《自序》中说,“虽然中外人士们,现在只有很少数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受了这么隆重的纪念,然而他死的时候(一八五五年),梁发这个名字,已洋溢于英美的教会了。”[8]麦沾恩没有低估梁发的意义,却把他产生影响的时间定得太迟。早在1834年,裨治文就在英文的《传教先驱》杂志发表长篇文章,介绍梁发的生平和事迹了。[9]那一年,四十七岁的梁发已备受关注。
美国费城的长老会出版部曾于1842年出版一本名为《传教士的故事》的书,是专为教会内的儿童读者编写的读物。此书共讲述了十五个故事,涉及各大洲多个国家的传教先驱人物。其中第七个故事共12页,主人公就是中国的梁发,并且提到了他的儿子梁进德。[10]伯驾医生在广州眼科医局的年报中,也多次提到梁发。[11]
△ 梁发《日记言行》(藏于伦敦会档案)
梁发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教会。1841年1月31日,伯驾在华盛顿向参、众议员演说时曾引用过梁发的话,并说:“梁发甚愿在此医院中服务,因为他曾患险症,中国医生都以为无救,可是竟在此医院中医愈。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过其他善功,只恢复了这个为上帝所爱的仆人的康健,我也已经不枉为一世的人了。”麦沾恩为此感叹:“梁(发)先生在美国历史上也有位置”。[12]
到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洪秀全与梁发所著《劝世良言》的关系,更是成为英美教会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麦都思为此在1853年的英文《北华捷报》上连载长文,讨论梁发对洪秀全的影响及梁发的传教贡献。洪仁口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笔录的The Visions of Hung-Siu-ts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书于1854年出版于香港。书中颇为生动地讲述了洪秀全与梁发的相遇及赠书情形:
翌日,秀全在龙藏街又遇见二人。二人中,其一手持小书一部共九本,名《劝世良言》。其人将全书赠与秀全。秀全考毕即携之回乡间,稍一涉猎其目录,即便置之书柜中;其时并不重视之。……一八四三年秀全教馆于离本乡约三十里之莲花村(Water-Lily)之李姓家。时在五月,其中表李某一日观于其书柜,偶于其藏书中抽出《劝世良言》,随问秀全其书之内容。秀全答以不大知得,此书为曩时到广州赴考时人所赠送者。……《劝世良言》一书,对于秀全之思想及行动影响至大。吾人试研究其内容,著者自署名为“学善”,而其本名实为梁发,其人则米怜博士(Dr. Milne)所指引入基督教之中国教徒也。[13]
以上有关梁发的报道及讨论发生时,梁发本人尚健在。这些郑重其事的描绘,大约会以各种渠道(如英美差会通过在华传教士转达、梁发之子梁进德在阅读英文报刊之后转述,等等)反馈给梁发,这对梁发无疑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梁发确是基督教新教第一批中国信徒中最有成就、最具影响的一位。
△ 梁发《劝世良言》(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基督教新教的传入是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交织在一起的。对于传教士引介的西学,中国士人表现出了足够的敬重和兴趣。世俗层面的西学虽被中国士人所接受,然而传教士与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却是命途多舛。梁发的身后命运,是与基督教的中国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是民国知识分子的反教思潮勃兴;一方面是不断壮大、不断本土化的教会系统对先驱人物的感念与追怀。当然,不少世俗知识分子虽然反教,却对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不无好感。这两股力量共同促成了民国时代对梁发的二度发掘。梁发原先只受到英美教会的重视,到“中华教会之自立”形成一定气候和规模之后,作为中国教会之“先进者”又重新受到重视。教会系统在回顾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时,再次发现梁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角色。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史研究界在追溯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之来源时,也一再地述及《劝世良言》的影响,梁发的重要性在中华民国时代再次得到凸显。1923年,香港教会机关《大光报》刊印《中华基督会第一宣教师梁发先生传略》,作为“全国青年会第九次大会赠送纪念品”分发。此《传略》由皮尧士、张祝龄二人合译。
土肥步称这一现象为“19世纪的中国传教士梁发”在20世纪的“被‘发现’”,[14]在这个过程中,麦沾恩所写的《梁发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麦沾恩说,“梁发现在已经不止是属于中国的教会,并且简直是属于全世界的教会了。”[15]麦沾恩的话自有道理,只是他未免把逻辑顺序说反了。梁发先是属于英国的伦敦会,之后才属于“中国的教会”。因为梁发所依托的是广州及港澳地区的西人社区。梁发两度遭到官方的逮捕,“中国”对他而言亲切而又可怖。梁发虽是中国人,但在文化、宗教和职业上,他已经越出“清朝”的体系之外。“清朝”自然也不以他为荣。
△ 梁发《真道问答浅解》(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皮尧士、张祝龄二人合译的“梁发传略”称梁发所写《救世录撮要略解》为“基督教汉文小书之破天荒第一册也”;[16]在谈到梁发的著述时,皮尧士、张祝龄感慨道:“译者考梁君先生著述及多种印制品,莫不佳妙。惜其书目尚能考据,惟欲觅其原书,恐不可得矣。”[17]
梁发因为与英美传教士接触更早,所以他不光写下“基督教汉文小书之破天荒第一册”,还是较早翻译西方农学著作的人:
一八三七年,梁发先生从事一种新工作,他襄助美国公理会的杜里时(Tracy)牧师翻译一本小书,名叫《新加坡栽种会敬告中国务农之人》。梁发熟谙农事,他从小对于农事已经很有兴趣,这时杜里时请他襄助翻译一部对于农人有切实供献的书,自然是他所极愿为的了。非但如此,他还做了《鸦片速改文》一书,劝人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语极痛切。[18]
引文中提到的这本名为《新加坡栽种会敬告中国务农之人》的书,是梁发协助帝礼士译成中文的。但这个书名,是胡簪云据麦沾恩的英文梁发传记回译为中文的。据伟烈亚力所记,书名为《新嘉坡栽种会告诉中国做产之人》,这应该是帝礼士、梁发的原译书名。[19]梁发襄助帝礼士翻译农学著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以往很少注意到梁发在翻译方面的贡献,这本书足以证明梁发在农学、翻译等领域也曾有所作为。
梁发的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他自己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大约十分有限,但他长期生活在由英美传教士组成的社群中。这个社群的交际语言是中、英双语混杂的。传教士们的中文读写能力参差不齐,梁发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适应这种双语交织的环境。传教士也会有意识的教给他一些基本的英语概念。梁发1820年1月至1821年5月曾在米怜主持的英华书院修习神学。据米怜致马礼逊信中的描述,梁发在英华书院的“高班”;米怜说,“从去年(1819年)开始,我给就读的学生一些英文概念。我每天教两三句,希望一俟他们学会一百个单字左右,就可以跟着教他们这种语文了”。米怜又说,“一周五天,我给阿发(即梁发)逐章讲解马太福音,为时二十到三十分钟,俾增进他的学识”。[20]
△ 梁发石印的《西域古经格言》单张(伦敦会档案)
1813—1814年,马礼逊印出2000本新约圣经。[21]麦沾恩曾经提到,梁发故宅里的文件和书籍由于1915年的水灾而散失无存,但在梁发身后的遗物中,“幸而还留存了这大宣教士的一幅画像和他所用的那部一八一三年在广州地方出版的马太福音。”[22]米怜为梁发逐章讲解马太福音的时候,梁发手上当是持有一本马礼逊的马太福音中译本的。这个时候,梁发手中的马礼逊译本差不多只是一个“道具”,米怜大概要越过马礼逊的译文(马礼逊本人也不满意他经手出版的译本[23]),依据英语原文向梁发进行口头讲解。米怜的讲解过程,既是基督教知识的传授,也是两种语言的研习。后来梁发回国,又长期和马礼逊交往。比如说1833年这一年,梁发和马礼逊朝夕相处:“梁阿发、朱先生和屈阿昂,加上李先生,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和马博士住在一起,每天听他的教诲,扩阔自己对上帝真理的认识,增强自己的信心。这样,他们便可以因自己有得救的智慧而去教导别人。”[24]不知道梁发究竟掌握了多少英文概念和单字。退一步讲,即使梁发不能熟练掌握米怜教他的英文概念和单字,至少他对英文是有所了解的。也正是在1833年,马礼逊和梁发都开始决心为中国创造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宗教文学”:
上述列举这五个用中文的国家(马礼逊指的是中国、高丽、日本、琉球、交趾支那——引按)很有可能占全球人口三分一以上,他们早就知道使用文字,有文学作品,懂得印刷术最少有七百年。不过他们的文学作品要么是神仙佛道,要么是不信鬼神,或是诲淫放荡。严肃作品除了反对宗教或庸俗的迷信外,没有甚么东西可以教人;而轻松文学除了荒唐之事或酒色财气外,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人。从人的角度来看,要振兴中国,最不可少的,首先是培养大批的基督徒中国学生,俾可从中产生优秀的作家(good writers),为中国创造有启发性的宗教文学(religious literature)。[25]
此处所说的“宗教文学”(religious literature),排除了基督徒所谓的“异教文学”,所以并非广义上的“宗教文学”,而是特指“Christian literature”,即体现着基督教精神的那种“文学”。“literature”固然也有广义、狭义之别,不过马礼逊心目中的“优秀作家”及“有启发性的宗教文学”,还是颇为接近或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的。
△ 梁发石印的《功过格之谬》单张(伦敦会档案)
马礼逊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当然并不只是偏见。马礼逊将中国文学分为“严肃作品”和“轻松文学”。他的评价标准不只出于基督教的标准,也有“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标准。马礼逊认为,“佛和道不够重视伦理,孔子则忽视宗教,而耶稣却把这两样连结起来,臻于至境。”[26]马礼逊心目中的理想文学应当重视伦理、重视宗教、关心来世、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他说,“基督教的通则是要提升人的气质和尊严”;他批评中国不如英国,因为英国人“有较多的脑力活动,可以高谈阔论国家的福祉,筹组慈善团体、文社和学会,此外又有报纸、月刊等”,“这多少都会启动、锻炼及强化智能”,而中国“则完全禁止讨论国家的施政,人民任何形式的结社都不受欢迎;对科学的研究没有兴趣,也不关心人类的一般事务;有财有闲的人毋须工作,通常(我不愿说永远)只好抽大烟虚度时光,或者纵情于最堕落的肉欲。”[27]马礼逊的中英比较观,涉及宗教、政体、道德、文明、文学等诸多层面。
一言以蔽之,马礼逊希望创造一种有信仰的文学,他心目中的理想信仰是基督教;他所欣赏的“有信仰的文学”自然也就是基督教文学、新教文学。马礼逊的中译圣经、梁发的宗教写作,是可以视为一种“有信仰的文学”的。梁发能够成为一位“基督教新教文学”(Christian literature)的“优秀作家”(good writers),肇端于他与马礼逊的相遇,在时间上要追溯到1811年,这是马礼逊到中国的第五年。前一年9月,“马礼逊先生的圣经译本已经达到可以付印的程度。他预备先印《使徒行传》一千部。……此书印刷由马礼逊先生的华人助手蔡卢兴先生经手。”这次印刷,梁发并没有参与。到1811、1812年,“两年中,马礼逊先生把《路加福音》和《新约》书信之大半付印,而此等书籍之雕刻及印刷多出自梁发之手。”[28]
通常认为,梁发之受洗入教与他从事圣经印刷的经历相关。但这不是全部原因。据梁发自述,他之信教并不全然归因于他所阅读的基督教书籍,也与佛教经书的阅读以及与佛教僧徒的接触有关。梁发由不信教到信教,在思想上经历过几次变化。(1)梁发的造笔、雕版及印刷技能,使他获得了从事相关职业的机会,从而有了阅读基督教书籍的可能性。1815年4月17日,梁发随米怜启航前往马六甲,次年11月3日在米怜处受洗。麦沾恩就认为,梁发在马六甲成为“热心慕道”之人非属“偶然”:“他以前与马礼逊先生所发生的接触和他雕《新约》书板中所认识的真理都对于他的心灵有着影响。”[29](2)由浑浑噩噩到“自知有罪”。如麦沾恩所言,这个过程当与他跟基督教书籍的接触有关。梁发说,“我未信救主之前,虽然自知有罪,但不知如何而能获救。”见神就拜是梁发这一阶段的思想特点:“我每逢朔望,必往庙内参神,求神保佑,但我身虽拜神,而心则仍怀恶念,说谎及欺骗别人之念永不能离我之心。”[30]
这是在他随米怜前往马六甲之前的思想状态。这意味着,虽然他已接触马礼逊、经手了新约圣经的印刷,但他也只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有罪。所以到处拜神,拜各式各样的神。(3)佛僧启迪梁发探寻救赎之道。梁发对佛教的了解,以及对佛教书籍的阅读,是他归向信仰之路的一大契机——尽管他后来在《劝世良言》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佛教。梁发在马六甲固然常听米怜宣讲经义,但并无兴趣:“我虽然参与彼之叙会,然我之心实不在此也。有时我看彼等之圣经,且听彼解释,但我却不能完全了悟其意义。”直到几个月后,有位佛教徒从中国来到马六甲,住在离梁发不远的观音庙中。
该僧与梁发经常见面,梁发问他:“我要如何,罪方得赦?”僧答:“每日背诵真言,则彼在西天之佛将赦尔全家之罪矣。”梁发听罢,“一心想做一个佛教徒。此僧赠我佛经一卷,嘱我每日读一回,说如我能念至一千遍,则以前一生罪过都可以抹除。此后我遂每日背诵此经,……”[31](4)求赦愿望促使梁发对佛经、圣经发生浓厚兴趣,在对比阅读两教经书后改信基督教。梁发说,“同时,我又闻传教士等由耶稣而得赦罪之说,在闲暇之时我又自己查察圣经,见经中严禁不洁,欺骗,拜偶等罪过,于是我想:‘此是一部劝人离恶之好书。……’此后我遂留心听人解释圣经,而安息日读经时亦更为注意,而且求传教士为我解释。”不久之后,梁发愈信基督,“我自念我是一个大罪人,如不赖耶稣功德,上帝又焉能赦我?于是我遂决志为耶稣之门徒而求受洗矣。”[32]
△ 《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佛教、基督教共有的求神赦罪观,启迪梁发省思自身过往经历,兼及信仰与道德问题,他由此确信自己有罪。而在对照阅读两教经书的过程中,梁发对基督教的兴趣日增,对佛教的好感日减,并最终摒弃佛教。梁发之受洗入教史,实是一部中国最下层平民读者对佛经、圣经的对照阅读史。
基督教新教早期来华传教士如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等人都曾为中文圣经译本的“文体”(style)问题所困扰。马礼逊来华不久,即着手翻译新约圣经,同时编纂字典。“在安息日,除了积极从事公务外,另一个重要的话题盘据在他的心中多时,即翻译圣经为中文,用甚么文体才最为合适的问题。”[33]马礼逊把思考的结果告诉了米怜,米怜记道:
在中国的经典中,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文体有三种:深奥、浅白和中间路线。《四书》、《五经》所采用的文字非常简洁,被认为是经典式的。大多数较为轻松的作品,像小说,是完全用通俗的文字写成。备受推崇的《三国演义》,就文体而论,介乎这两者之间。他(指马礼逊——引按)起初倾向于中间路线;但后来他看了《圣谕》之后,就决定加以模仿。圣谕在各省的公众大堂一个月宣读两次,旨在教导百姓人伦关系及政治责任,读时用极为通俗浅白的文字加以解释,因此:第一,更易为老百姓明白。第二,在大众面前宣读,浅显易懂,而深奥的经典文体则否。中间文体在大众面前朗读也清晰易懂,但却不如浅白文体那么容易。第三,讲道时可以一字不变地加以引用,且毋须任何解述百姓也听得明白。然而,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了中间文体,因为无论在哪一方面,这才最适合一本为一般读者而设的书。[34]
这段话表明马礼逊在浅白文体、中间文体间的徘徊。虽然据米怜所记马礼逊的最终选择是中间文体,但事实上马礼逊一直强调翻译圣经要采用“浅白文体”,这证明他的选择是“Low Style”,并非米怜所说的中间文体(“Middle Style”)。
△ 伦敦会档案所藏马礼逊手迹
1819年,与米怜合作译完旧约圣经的马礼逊给伦敦会董事会写信,表达了他对“俗话”或“白话”(“Sǔh-hwa, or vulgar talk”)的偏爱:
中国人的“俗话”一向为文人所轻视。俗话并不意味“粗俗下贱”,乃是百姓的用语,有别于只有博学之士才看得懂的那种高贵、古雅、深奥的文体。正如欧洲的学者在过往较为蒙昧的日子里,认为一本体面的书多少都要用拉丁文著作一样,中国的学人亦认为正经的书不可用白话。朱夫子写他的理学确实是打破了传统,因为要传达新思想,不能不用最浅白的文字。……若是为了取悦有识之士,或炫耀一己的满腹经纶,而采用这样深奥的文体翻译圣经,就似乎是在重复埃及祭司的做法。据说他们以象形文字书写教理,好叫除了他们自己或一小群受戒者外,就没有别人看得懂。……这样的贬斥也许是过于严厉了,但翻译圣经当用浅白及简洁文字为原则,却非充分肯定不可。[35]
马礼逊这番话,与后来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见地相同。胡适说:“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36]虽不能说马礼逊的白话译经是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至少可以说,胡适所提倡的著述宜用白话及“言文合一”,马礼逊早在一百年之前就已在中国的广州、通过中文译经的方式付诸实践。
马礼逊的主张是采取浅白的文体翻译圣经。不过,马礼逊并未能很好地实践他自己的主张。因为他的中文能力有限。1843年10月26日,美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娄礼华应他父亲娄瑞(美北长老会秘书)的要求,写信报告他本人对马礼逊圣经译本的看法。娄礼华说,我在此前给您的信中就曾说过马礼逊博士的译本很不完善,中国人读不懂。父亲您曾说,既然马礼逊的译本如此不完善,我们何时能有更好的译本?娄礼华遂分析马礼逊当初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认为马礼逊是第一个开始学习中文的新教传教士,他学中文时缺少帮助,不得不自己动手去编语法书和字典。马礼逊又在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这使他难有充裕的时间翻译圣经。他担任翻译一职时平常接触、使用的语言,无非是钱来钱往、讨价还价,翻译圣经可不宜用这些语言。尤为重要的是,他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尚未完全通晓中文,是边学边译的。娄礼华充分肯定马礼逊的开创之功。认为马礼逊的声名将赖其《华英字典》而非中译圣经以传。[37]
梁发并非饱读诗书、才思横溢之人,却在这个历史关口赢得了机遇和舞台。伟烈亚力所记的梁发著述有:(1)《救世录撮要略解》,共37页,广州,1819年版。(2)《熟学真理略论》,9页,广州,1828年版。(3)《真道浅解问答》,14页,马六甲,1829年版。(4)《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共3卷,广州,1831年版。(5)《劝世良言》,9份小册子的合集,经马礼逊修订后在广州出版,1832年。(6)《祈祷文赞神诗》,60页;澳门;1833年。(7)《论偶像的虚无》,宗教传单,摘自《以赛亚书》第44章。伟烈亚力称,“这些仅仅是我们所记录下来的阿发出版发行的作品,并非他在传教过程中所出版的全部著作”。[38]
上面提到的梁发著述中,《圣书日课初学便用》是英国海外学校协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的圣经教程的中译本,第1版问世于1831年,第2版则由该协会出资,于1832年出版。《祈祷文赞神诗》共60页,其中赞美诗为马礼逊等人所写,而“祈祷文”44页,则是梁发创作的。[39]这些著述,中国国内的图书馆鲜有收藏,足见梁发之不被国人看重由来已久。
另外,米怜在马六甲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也有梁发撰写的稿件。[40]梁发应也参与了这份中文杂志的编纂。[41]《鸦片速改文》《新嘉坡栽种会致中国农学家》这两篇挂在帝礼士名下的作品,也是梁发协助创作或翻译的。[42]所幸的是,梁发的不少著作如《劝世良言》《拣选劝世要言》《鸦片速改文》等,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均有收藏;[43]该馆还藏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求福免祸要论》,前者是梁发参与编纂及撰稿;后者署名“学善居士纂”,或亦出梁发之手。[44]
△ 马礼逊译《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在中国,想要劝导他人,最好的办法不是说(speaking)而是写(writing),这是他们的习惯(custom)。所以梁发用中文写了一本小书,讨论灵魂获救的方式问题,并且印了出来。”[45]这表明,梁发自己撰写布道读物的做法,也令西方人认识到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阅读与写作传统。
关于梁发的“文体”,密迪乐和麦沾恩有不同的评价。密迪乐认为:“梁发的文体反映着热诚和牺牲的精神”,这是肯定的一面;密迪乐又紧接着否定梁发说,“他的文体大部分是建立于那与当地言语不合的圣经译文和他的外国雇主所作的神学论文之上的,因此,他的作品很是晦涩,令人不堪卒读”。[46]麦沾恩所引密迪乐对梁发的评价,胡簪云的中译本没有注明出处。麦沾恩的英文原著在正文中是提到出处的,那就是密迪乐所写的“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一书。
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作者是Thomas Taylor Meadows(麦沾恩译为“美都司”,时任广州英国驻华领事馆翻译,本文称密迪乐)。[47]其实,密迪乐对梁发的评价并非出自他本人,而是借鉴了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的话。密迪乐谈到梁发时,重点讲了三点:(1)梁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having had little previous education);(2)梁发的文体深受传教士中译圣经的影响(formed his style in a great measure on the unidiomatic biblical translations and theological tracts of his foreign employers);(3)晦涩(somewhat unclear),令人不堪卒读(repulsive)。[48]
△ 梁发1830年写给伦敦会的信(马礼逊英译)
麦都思在三年前的《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上已发表过相似的观点。麦都思的主要观点也是三个:(1)(那本书)的总名是《劝世良言》。……看不出梁发曾受过完整的教育。(“The general title is 劝世良言 Keuen-she-leang-yen, Good words exhorting the age……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Leang-afa ever had the advantage of a thorough education”);(2)梁发时常受雇刻书,这让他多识了不少字。然而并没有提高他的中文能力。他受雇刻印的书是翻译过来的,带着外国人的腔调。(“His having been constantly employed about books somewhat increased his acquaintance with letters. It has not, however, tend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his style in Chinese, that the book which he was employed to print, was a translation from a foreign tongue …”);(3)遣词造句不符合中文的习惯(“phrases drawn up in unidiomatic Chinese”)。[49]
麦都思的这些观点,完全为密迪乐所照搬。但是,麦都思、密迪乐对梁发的上述评价是有问题的。麦沾恩不同意密迪乐的评价:“这种批评未免太苛刻了些。”[50]麦都思批评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喜欢征引圣经的段落,有时甚至是整章征引,这些都是对马礼逊、米怜译本的逐字逐句的照搬;他又批评梁发,“附在后面的解经文字,跟他手上的教科书在文体风格上没有两样,像极了他在教堂里听惯了的面向大众的散乱的布道演讲。这些原因,造成了他文体上的极端散乱、冗长乏味及词藻的纷杂。”[51]
△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救灵获福文》手稿(作者不详)
麦都思对梁发的批评着眼于两个层面:一是他的教育及中文写作水平;二是他的“文体”,包括文风及遣词造句等。关于梁发的教育程度低,这是个事实。不过,这个问题如果反过来看,正可以表明梁发的可贵。这是他的特殊性。一个并未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仍能写作和出版自己著译的作品,这不正是梁发的意义吗?麦都思从“文体”角度对梁发展开的批评,恰恰是梁发有所建树之处。
关于梁发《劝世良言》一书的文体,以及该文体与传教士圣经中译本的关系,麦沾恩说,“梁发引用那与当地言语不合的圣经译文,乃是出于不得已,他深知这译文的不善。”[52]梁发本人早已发现马礼逊圣经译本在文体及表达上的问题:
他(梁发)曾经论及此事说:“现在圣经译文所采用之文体与本土方言相差太远,译者有时用字太多,有时用倒装之句法及不通用之词语,以致意义晦暗不明。圣经教训之本身已属深奥神秘,如再加以文体之晦涩,则人自更难明了其意义矣。我为中国人,我知何种文体最适合于中国人之心境。吾人须先努力将译文修正,使其切近中国方言,然后将其印行。虽然读者信仰圣经或反对圣经系另一个问题,初与文体之晦明无关;但吾人总应竭吾人之力使圣经之文字易于通晓耳。”于此可见梁发实在是深知圣经译文之不完善的。[53]
梁发的话表明,马礼逊圣经译本的“意义晦暗不明”,原因是用字太多、倒装句法及生僻语词的使用。梁发为此做了三方面的努力:一是向伦敦会或身边的传教士表达他的意见。他曾写信给伦敦会的秘书(由他的儿子梁进德译为英文),批评伦敦会总是派出中年的传教士来华,这些人口舌僵硬,无法适应中国口语的特性,而且他们总是太过于着急写书。他们所写的书,中国人很难读懂。不如派些七、八岁的孩子,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学好中国的书面语(written language)。[54]二是着手对圣经译文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正。他曾将新约全书中应该修改的地方“列成一表献示米魏茶牧师”。[55]三是在自己的撰述中对马礼逊的译文进行详尽的解释。《劝世良言》中的不少章节就是先引马礼逊的圣经译文,然后加上他自己的解说和评述。麦沾恩赞曰:“他著作小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用切近的譬喻和通俗的文字来解释圣经,使人们明白圣经的真意。这些小书的文字并不如美都司所说那样的缺乏文学意味,我们只要看当时的学者都很注意他的书,就可以知道他的书做得不坏了。”[56]
△ 梁发逝世后,其子梁进德写给伦敦会的信
即使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读者,也能从梁发所写的宣道读物中读出一种对待人生、世界、天地万物的虔诚与敬畏之心,这便是密迪乐所说的“热诚和牺牲的精神”。这种虔诚与敬畏,是对中国文学精神、文化精神的补益。马礼逊、梁发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还有另外的层面,即他们对于中文书写的白话性、平民性的强调。这是他们在中译圣经的过程中遭遇并力图解决的命题。这一命题初衷在于传教,不过也产生了文学上的意义。至于如何从“文学”或“近代”的意义上界定、评判梁发所写下的文字,取决于我们对“文学”或“近代”概念的认识,以及我们所取的标准。无论是否认可这些文字为“文学”,它作为十九世纪中国的一种“Christian literature”,都已然是一种客观的文学存在。无论梁发本人是否被认可为“文人”,他的作品都已产生了客观的历史反响,启发我们重新思考“近代文学”的作者、文体、边界与起源等问题。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宗教翻译文学:近代以来理解梁发的不同思路》,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